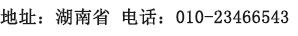樊强爷爷的花圃被樊强搬到城里去了。最近这件事在金水村传的沸沸扬扬,樊强出息了,在城里已经安家落户的樊强,想把爷爷留下的花圃移植到家里的后花园里。
团团簇簇的石竹花颜色艳丽,矮牵牛伏地而行,各色的月季、海棠争相绽放,给北方还没有完全觉醒的初春添了好些颜色。这些花朵因为长久地失了人的照顾,没有剪裁枝丫,野野地生长着,就那样呼吸着一冬又一冬的冷空气和冰雪,应是历经了不少磨砺,所以枝干看着比同类的更加粗壮,花色也更加妖冶。金水村的村民们看着樊强带领着工人们把一株株话小心挖起又小心地拿塑料袋裹起,排列着放到大卡车里,那些离开了泥土的花儿仍无知无觉地开着,随着初春的寒风左右摇晃着,在塑料袋里摩擦出沙沙的声音。
樊强记起爷爷还在世时,樊强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看着爷爷在他珍爱的花圃里为他的花儿拔草除虫浇水,爷爷常常在花圃里一待就是一下午,樊强在旁边一看也常常就是一下午。要说樊强爷爷的花圃里有多少花,有哪些花,说来其实也只是一些乡下很常见的花,有的是爷爷在山上挖来的,有的是路上随手采的,有的是爷爷的学生送来的,听说还可以入药。这些野花经过爷爷一手的精心栽培,个顶个的水嫩鲜艳,枝丫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夏天常附着满了蜜蜂和蝴蝶,晚上萤火虫点亮了一整个花圃,白天缤纷多彩的花朵此刻在夜里都散发着奇异的光芒,常常看呆了樊强。在樊强的认知里,在金水村这片山沟沟里,他爷爷的花圃是唯一一个有颜色的地方,金水村里连山都是灰色的。
爷爷一直和村里人不一样,这是樊强自打出生就知道的了。村里人都是黝黑黝黑的,唯独爷爷一张脸是白净的,手指也是白的,中指还带着薄薄的茧。这也许是刚出生那会的樊强最喜欢被爷爷抱的原因。其实樊强也喜欢母亲的怀抱,只是父亲在工地上出了事故后母亲便匆匆忙忙改了嫁,之后樊强再也没有依偎过母亲的怀抱了。只剩下爷爷和樊强相依为命。爷爷教樊强认字,背三字经,带着小小的樊强去他上课的学堂,和高年级的孩子一起坐在最后面听课,那个学堂还是爷爷一手创办的,他说服乡亲们送孩子到学堂读书学知识,自己则一人包揽了所有的课程教学,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停歇,后来学堂停了,村里只有樊强一人每天走着十几里山路去镇上念书,其他的孩子都回家帮家里种田了,村里人对樊强爷爷的“脑袋”不理解,樊强的爷爷不和村里人来往。那时爷爷每天去山上挖草药,卖给村里需要治病的人,或者去镇上的医疗所换钱,就这样供着樊强一直念上了大学。这期间,爷爷的花圃一直维持原样,没有变过。花圃里的花总是呈现着欣欣向荣的景象,即使冬天被雪花覆盖了,也有着冰清玉洁中别样的美丽,来年春天又马上抽枝结冠,拥挤着开满一整个花圃。
樊强长大后才知道爷爷原来是南方人,曾在南方居住过,后来被分配到金水村劳动改造,遇上了樊强的奶奶,于是在这里扎根下来。爷爷最喜欢和樊强讲南方,那个水田一望无际,金穗子垂着丰收的喜悦,到了秋天,到处是稻香蛙叫,连天空都是金色的南方。在樊强的心中,没有比爷爷口中的南方更好的地方了。樊强吃腻了土豆,幻想着有一天也能吃上一碗香喷喷的一粒粒还冒着热气的白米饭,还想去爷爷曾经待过的地方去看一看。后来樊强去看了,果然是金色的天空和金色的稻田,只不过并不是农人在收集这些秋天的硕果,一辆辆轰隆隆的收割机在金色稻田里留下整齐的印记,边向前推动着吞进那些沉甸甸的金穗子……
爷爷的花圃已被搬空了一半,其实樊强自从工作以后,很少回金水村了,工作第一年回来了一次,没有待多久就回去了,那时村里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了,都出了金水村打工去了,樊强给爷爷留了一部手机,方便联络。第二次回来是送走了疼爱他的爷爷,第三次是来搬走爷爷的花圃……如今樊强也算是成功人士了,然而这些年心里却越发的不踏实,睁眼闭眼竟全是爷爷花圃里的那些花。春天的花圃,夏天的花圃,秋天的花圃……总在樊强的眼前一一闪过……
“这是什么?”“竟然有东西埋在花下面?”工人的讶异声唤醒了沉醉在记忆里的樊强,走下花圃,竟然发现下面埋了许多书,有教过樊强的三字经,爷爷当老师那会从镇上买的数学课本,还有一些外文名著,这些书被小心地裹在灰布里,封面上的字还能勉强辨认,内容却全被雨水腐蚀了,黑色的墨晕开了一层又一层,似一朵团簇开放的黑色花朵。樊强看着这一簇簇的黑色花朵,不禁眼眶湿润,原来爷爷看了几十年的花圃,不单是看他的花啊,还有埋在花下的,那生生不息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