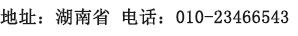凡是回不去的,都称之为回忆。不堪的回忆,我们选择尘封;开心的回忆,谁也无法忘却;总有一些回忆,会在不经意间浮现,不痛不痒,却*牵梦绕。在朋友圈中,时常看到回忆郭磊庄中学的文章,这所不在了的学校,承载了许多人的青春韶华。或许,正因为他不在了,回忆无处安放,才更有了纪念的意义。
郭磊庄中学大门。那所学校
那是所不大的学校,一届四个班,每班50人左右,从初一到初三,外加一个人数不多的高中班,全校六七百人。这是所辍学率很低的学校。当时刚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各个乡镇的普通初中辍学率很高,入学时满员十几个班,能坚持到初三毕业的只有区区几个班的人数。而当时的郭磊庄中学,到初三时,还能保有80%的班额,每个班的建制还在。那个时候大学生很吃香,但很多人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撑不到上大学。
那时周边的人,都还困在土地上,外出打工的人不多,人不活泛,眼界、心胸也受到了限制。是的,贫穷限制了这一地区人的想象。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择校”,不流行“学区房”,好多人没去过县城,只知道柴沟堡是个很繁华的城镇,一切似乎还处在蒙昧状态。父辈们语重心长地教导孩子,“好好学习,别再种二垄子地”。想出人头地,想靠知识改变命运,生于斯、困于斯的人们,把郭磊庄中学当作了地区圣殿。小升初,郭磊庄中学实行选拔性考试。适龄人,以上郭中为荣。
《我的青春期》拍摄地是郭磊庄中学。年,我入郭中。离家34里(不是公里)的学校,对于一个从未出过门的孩子来说,是个好陌生好遥远的地方。入学,要求自备行李,自带储物箱。那时没见过浴巾、不知道有夏凉被,只带一个适中的花被子、一条褥子、一条毡子,卷巴好了塞在洗干净的化肥袋中,用麻绳五花大绑绑在二八自行车的后架上。另外,得准备一个平时放东西用的箱子,学校不提供储物箱。这个箱子,因为不是统一定制,也没有尺寸的硬性要求,所以五花八门,或高或矮,或胖或瘦,花花绿绿,如果把所有人的储物箱都摆在一起,一定蔚为大观。
《我的青春期》里面再现了我们的手工储那时,村里不通汽车,出村的人人手一辆自行车。而这种家庭必备的交通工具,不像现在的孩子,从三岁到大,根据不同的身高、年龄段会有不同的尺寸,我们那时管你多高,管你够着够不着,都是统一的,二八,二八,飞鸽,飞鸽!身高所限,脚踩到脚蹬子都费劲,为了驱使它前进,你得大幅度利用自己的臀大肌,调整左右腿的前倾度,通俗来讲就是,扭屁股。
《我的青春期》剧照。二八自行车。开学的日子到了,四面八方的孩子,骑着不相匹配的车子,驮着奇形怪状的箱子、花花绿绿的被子,怀着忐忑的心情,更怀着求知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期望汇聚到了郭中。
郭磊庄中学的门不大,简单而普通。教室、宿舍、办公室都是一排排的平房,校园里还都是泥巴路,每边教室的左右两边都有一条水泥制的凹式水渠用来通水。教室区在南边,校园中间是一个小广场,土堆垒起来的小高台用石块围着,这就算是礼台了。由南向北,广场的左边是行*办公室,水房、伙房(做饭的地方,仅是做饭,没有地方让你吃饭,因此不能称为食堂),还有一间校园广播室。广场右边是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女生宿舍,依稀记得有三排,每排宿舍旁边整齐地码着一辆辆自行车。女生宿舍南边是全校的 一个小卖部,店主叫谢老三。再往北,是原生态操场,纯泥巴造,说是原生态却又是寸草不生。操场北边是一大通排房子,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是男生宿舍。
郭磊庄中学校园一角校园不大,分区错落有致,一时间被汇聚来的孩子和送孩子的家长弄得喧哗、热闹起来。我们操着差不多的口音(不能说一样,因为有些人平平地说“二”,有些人却要张大嘴巴说“儿啊”),生涩地见面了。
办了入学报到手续,接下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去宿舍占坑儿了。家里都是纯土炕,在来这里前,我没睡过床,今天就要离家睡床了,兴奋。宿舍的木门敞开着,里面已经有大人在帮孩子整理床铺。在这里,我见到了接下来三年要与之休戚与共的床。两间掏空房,南北两向各有一大排木板,是的,我们的床是共有的大通铺。北床睡13人,南床除去门的位置睡10人。青春的荷尔蒙将异常集中地在这里交杂。床是共有的,因此每个人的床被不能肆意摊铺,大人们小心地拿捏着分寸,左匀右挪,将那些花花绿绿们尽量均匀地躺整齐。我们的储物箱被塞在对应的铺位下,同样的花花绿绿。
《我的青春期》剧照。“花花绿绿”们大人们相继离开,我们都被抛弃在了这个陌生环境里,好无助。同村的孩子,聚在一处,让我们感到了什么是相濡以沫。晚自习前,按身高分类,我们都有了彼此的同桌。下晚自习了,人潮蜂拥,初一到初三的学生都朝宿舍走去。被裹挟在人群中,初来乍到的孩子在熙攘中感到了落寞。不熟悉路况,深一脚浅一脚,我竟把自己弄到了教室旁边的排水道里,横陈下去,和沟渠完美地贴合。惊*未定,已经被身边的同学扶了起来,善意地嬉笑着询问我是否摔伤。
入学 夜,新鲜,我涨了知识。听他们讲,挨着我们宿舍的是一个混合宿舍,而混合宿舍里面没有女生。
那群人,那些事
寄宿生活的开始对于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来说,是混沌的,一如食堂那口直径 米的饭锅,亦如那锅里分不清你我的熬菜。
开学的 天,每个宿舍可以领到一个超大的铝盆、一个大铁桶和一把勺子,这就是我们三年吃饭的家伙事儿。宿舍每2人一组,轮流执勤,订饭、打饭、分饭,前一周订下一周的饭,轮到订饭的人要提前到食堂前面的小黑板抄来下周的饭表,然后自制表格统计每个人每顿饭的量,早上几两粥,几张饼;中午几两饭,几两菜;下午几两馒头,几两菜。统计好后,按量收费,然后再将总数和钱报给食堂。下周起,一下课,就由值日的同学拿着家伙事儿去领饭回来,拿出订饭时的单单,挨个分下去。分完了饭,还要负责把大盆大桶洗干净了。这是件很锻炼人的事,教你负责,让你有责任心,还学会了统计。同时,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们那时的馒头比这大好多。食堂的大师傅,要做全校几百号人的饭,粥的稠稀和菜的多寡难免不太均衡。同样报上去五斤粥,可能 天领回来是半桶,但第二天领回来可能就是少半桶了,这可难倒了分饭的同学,分着分着有时就不够了,后面排队等饭的只能气呼呼地干瞪眼。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在早上打粥的时候,值日生自备一瓶开水,从食堂一领到粥,自觉地倒开水进去,如此,粥只多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都按量领到了所订的饭,但桶里面还有剩余,于是,值日的同学又招呼大家“补饭”,勺子再依次在每个人的饭盒中再来一次,有时候这种补饭可以进行好几回。嘿,花了二两的钱,领到了三两的粥,皆大欢喜。
真实场景如此,慢慢地,事情开始变味,反正要加开水,报多少都看不出来。于是,明明统计出来是五斤粥,但报给食堂却是打过折的,报上去的也许是4斤,也或者3斤半,除了饼、馒头和包子是计个的,这个马虎不得,其他的都可以依次减免。这仿佛成了一个不公开的秘密,每个人都心照不宣。
说到了吃饭,不得不提一下食堂的锅。那是一个大口径的锅,全校学生的菜都在那一个锅里烩,食堂的大师傅做饭,不用做菜铲子,用的是方头铁锨,是的,就是那种种地工具,郭中人都见识过。还有人看到过,大师傅用方头铁锨疏通外面的沟渠。我们无法证明是否是同一把铁锨,但我们打心眼里愿意相信他用的就是同一把铁锨。因为只有这样,才更野蛮,也更符合我们混沌的生活。
初三时开始用饭票,是不是很别致?郭中人的怪癖
“呲……噗!”“呲……噗!”……每个周日的下午,回家的孩子们再次扭着屁股从四面八方来到学校,把车推进车棚,锁好,俯身弯腰,找准气门芯的位置,拧下盖帽,拔出气门芯,听那“呲……噗!”的声音,一切发生的那么优雅,那么从容。整个下午,“呲……噗!”的声音在校园里此起彼伏,好一道风景。要是有人来问,你们在做什么,郭中人会骄傲地告诉他,我们在自个儿放气。这是郭中人的怪癖。
曾几何时,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好人,我们都心怀美好,直到我们遇到不美好的事情。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几个坏小子闲得蛋疼的时候,跑到车棚,手欠欠地拔了几辆车的气门芯,等回家骑车时,孩子们傻眼了,还有这么玩的?!自此,我们都学乖了,不给外人机会,自己动手。于是,就有了周日下午的“呲……噗!”音乐协奏曲,也有了周六回家时,排长队给自行车充气的另一番热闹。
事情就这样了吗,NO!我还遇到过更惊悚的,到车棚骑车时,车在,座椅没了,只留下那一个明晃晃的 笔直地杵在那里,任你零落。气门芯没了,花几毛钱可以买一个,事儿不大。可座椅没了,可是大工程了,我总不能屁股底下骑个棍儿回去啊。我被那种邪恶打败了,蔫了。后来,我的睡友知道了,“球也蓝不成你”,这种调侃的口气给了我信心,因为他传达给我这样的信息——“天空飘过五个字儿,啥都不是事儿”。接下来的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他拉上我,翻入了车棚,我们像阅兵一样审视那一辆辆瘪肚子自行车, 选择了一辆和我差不多半新旧的车下手。以暴制暴,我们是不是也非常邪恶?!
邪恶与否,待后人说。不过,至此,我和某一些人除了照例拔掉气门芯外,又多了一项工作——拆掉座椅。
校友画的教室外观,很怀旧的样子。郭中人舌尖上的美食
我们的青春,正值物质和金钱都匮乏的时代,对于吃的都有说不出的,由衷的喜欢。至今记得,郭中生活中最难以忘怀的好吃的有三样。
其一,薄皮大馅包子。包子皮薄如蝉翼,在猪油的浸润下,晶莹剔透,咬一口下去,油滋滋,唇齿留香。包子个头挺大,但我们无论自己的个头大小都可以狼吞虎咽,风卷残云,吃七八个, 的大胃王一顿竟吞15个之多,这个饭量现在看来都是惊人的;包子价格不低,平时吝啬的我们遇到包子总会大方一次。这种美食不是天天有,也不是每周有,是几周才轮一次,而且是周六的下午才有。这个时候,学校的大部分人都回家了,每个宿舍只剩两个护校的和一二个有事不回家的,食堂的大师傅这时才敢尝试做这一美食。但就是这一小部分人也爆发出了惊人的食量,大师傅们决定做包子是需要勇气的。周六下午,夕阳,映照着不再喧嚣的校园,落日的余晖,肆意在各处轻抹,忙碌的学习生活归于恬淡。我们抬着盆,盆里盛满了包子,一路小跑地回宿舍,盆里的包子也随着我们的运动,上下有规律地颤动着,各宣宣的(方言,形容面食松软)。
其二,稀粥泡方便面。当时是九十年代,方便面在我们当中得到了普及,不再是稀罕物,但用稀粥泡方便面可能是郭中人的独创。早餐很单调,天天是稀霍霍(具体是哪个字不详,形容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的小米粥和干笨笨的烧饼,是的,没过几天我们就腻了。去他的干烧饼,我们不要了。早上,值日生打回了和着开水的滚烫的稀稀粥(两个“稀”字强调不稠),我们早已把方便面饼平铺在饭盒里,一勺勺稀粥醍醐灌顶般倾盖在面饼上,肆意地浸泡着面饼,用不了几分钟,波浪型的面条开始松动,开始扭曲,和小米粥肆无忌惮地浑在了一起,不分你我。没有这么吃过的人,可能无法体会个中的滋味。那是一种独特的味道,被粥浸过的方便面,除保留了面的劲道,更进一步挥发出了小米特有的米香,再加上那两包佐料,饭盒中升腾起的丝丝缕缕,都是说不清的意犹未尽。
“美味”值得一生回味其三,学校门口有一修车铺,我们的气门芯大多从这里买,车子坏了在这里修,周六回家时也在这里一窝蜂地用打气筒给瘪肚子自行车充气,充一次气2毛,光这无本生意就有无限利润。那个摊主年岁比我们的父辈还要大些,但我们背地里都像其他大人一样叫他二软,尽管不合时宜。渐渐地,二软在我们身上发现了商机。待充气回家的孩子们,大多没有吃饭,充好了气都还要骑几里到几十里的泥路,是的,他发现——我们饿。周六一早,他就开始忙活,一摞一摞地烙馅饼,到我们放学时,尽管已经烙了好多摞馅饼,但从来没有意外,都是一扫而空。后到的同学,还得排队,等在那个只容半张脸的窗口,眼巴巴地瞅着平底锅中的未成品。馅饼,皮薄,尽管馅不多,但总有那么一点儿馅在一二处地方恰到好处地钻到了皮外,让我们看见。一双刚修过自行车,手背飘着*油味手底用白面着了粉底的手,拿刷子,蘸油,快速划过乌漆的平底锅面,继尔,一张张软趴趴的白面饼被*油手优雅地一扔,那个肉饼的上下两层在明显地呈现出肉动似的耸抖后无力地摊在锅底。“滋……滋……”,饼,贪婪地吸吮着油渍,呈现出由内而外的金*,袅袅烟气让归家的心不再那么急切。
二软的商机还在继续,我们美味也有想象的空间。周末我们有一天半的自由,学校的大门不再紧闭,学校中还有没有回家的孩子。二张小圆桌,几把小凳子,四平八稳地张在平底锅的后面,几平方的小房子,用“局促”来形容比用“拥挤”更加妥帖。我们见缝插针地围坐在桌子旁边,紧握双箸,眼巴巴地望向灶台,等那几道再平常不过的家常菜,尽管我们看到的只是二软的屁股。一道菜落桌,几秒的嘈杂,我们又继续眼巴巴地望着。
那时的我们很傻很天真,初一时,根本不知道二软的车店还有这种服务;初二时,我们知道了这种特殊服务,却不敢去尝试,一是没钱,二是之前谁也没有下过“馆子”,不敢去;初三时,除了那个高中班,全校我们 ,自以为升任天王老子了,逗钱去潇洒。但就是这种大餐,笼共也没去过几回。但或许正是因为少,至今还记得住。
读书,郭中人是认真的
郭中的学习和生活是浑然一体的,根本分不清你我。浑浑噩噩,却也认认真真。
早6:00,宿舍和教室通电亮灯。按理说,我们应该这时起床,但现实情况,亮灯的时候宿舍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是的,大部分孩子起得比鸡早。
夏天,6:00天已亮,冬天的6:00却还是乌漆一片。我们摸黑起床,囫囵抹一把脸,当然也有不抹脸的,再摸黑从宿舍到教室。“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一路上,我们不孤单,不害怕,因为总能看到一些模糊的身影,听到一阵阵或远或近的窸窸窣窣声。
没有灯的教室,偌大;黑色包裹下的教室,幽静。暗夜里,我们用蜡烛照亮。每一个跃动的小火苗陪伴着一个如饥似渴的孩子,昏*的烛光,熠熠生辉。一个火苗,二个火苗,三个火苗……东一个,西一个,前一个,后一个,就这样,我们的教室变得富丽堂皇。我们用烛光开启一天的光明。
《我的青春期》剧照。那时,我们很费蜡晚9:30,教室灯灭,宿舍灯亮。按理说,此时我们应该回宿舍睡觉。但现实情况是,灯灭的那一刻,大家下意识地,放笔、取蜡、点火(或者借火)、烧蜡屁股(不要问,为什么)、拿笔,几分钟的嘈杂后,我们归于平素,在富丽堂皇中继续一天的光明。晚10:00,宿舍灯灭,从这时至11:00,孩子们陆续归寝。那时的孩子很朴素,那里的孩子很用功。
学校不提倡我们挑灯夜战,但对于这种自发的勤奋始终没有制止。查寝的老师在宿舍找不齐的孩子,总能在教室里看到他们。久之,这成了郭中届届相传的传统和校风。谢老三的蜡烛也越发的好卖了。
校友绘的教室,原汁原味那些青春,那堆回忆
“深深太平洋底深深伤心……”“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刘德华、任贤齐、郑智化这些现在的“老人”伴随着我们的青春,早自习后、大课间都能听到那时的校园金曲,旋律是那么的动听,以至于我们不经意间哼出的都是不约而同的音调。记得有一年的国庆,学校在小广场上文艺演出,高中班的四个男生在台上合唱《笨小孩子》,我们听傻了,活人版的音乐真好听。那时,几乎人手一个随身听,都在装模作样,美其名曰学英语。但最倾心的还是放着天王的词带,百听不厌。在装模作样中,似懂非懂中,初中生活缤纷绽放着。
那个时候,有种叫作信的东西,带着成绩初一,浑;初二,沌
每人一个脸盆,说是脸盆,其实是多功能的,洗头、洗脸、洗脚、洗衣服、洗袜子、洗内裤、洗鞋子,凡是要洗的,都是那一个盆。现代人的世界可能无法接受,那时的我们觉得理所当然。
班上有位同学叫某一丁,不知是哪位好事者,信手在他的作业本上加了一道。数学老师可能对数字天生敏感:“作业作的不怎么样,妖蛾子倒不少,自己名字都不会写了?还某 ?!”加道的同学,你还在窃笑吧。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英语的?”“小学。”“幼儿园。”我们那代人,初中才开始有英语课,必考课,拉分课,噩梦自此开始,以至于现在的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