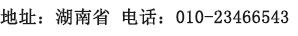板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说熟悉是因为这里是我的祖籍,我也曾在这里念书,也曾走过这里的每一条街道。说陌生,是因为我虽然在小镇上生活过,但我却从未真正意义上走进板泉人的生活日常。年轻时的我总觉得生活和梦想在远方。
虽是这样,隔的时间久了,就像有什么念想似的,总想回去看看,每每踏上这片土地,一种别样的情愫就萦在心头。
上个世纪60年代,为了生存,我的爷爷拖家带口闯了关东,后来家里的老亲又介绍了同为板泉人的母亲与父亲成婚,所以我们一家人,人虽在关东,但板泉的口音和生活习惯却一代代的传承。“出外东北腔,回家板泉话”,成了我们家人的标配。
年,望子*的父亲听舅舅说板泉的教学质量好,将我不远千里地送到了板泉,寄居在前村的二姨家求学,由此,我和板泉有了交集。
一、泉眼
板泉,确切的说应该叫板泉崖,是山东省莒南县有名的大镇。年郯城地震前称五姓官庄,郯城地震使原先的人口几近灭绝,后迁居之人重整家园,在村东石汪崖发现一处清泉,因破土之处是石板,从此更名板泉崖。我的先祖大约就是那时迁居板泉崖。
地震后发现的清泉位于何处,现在已无法考证。我记忆中的“泉”,都是在一条东西走向横穿镇中心的后河两岸。后河在我印象中是舒缓而清澈的,河面上有很多座红石板铺就的水漫桥。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要从水漫桥上经过。孩子们欢声笑语搭配那古香古色的小桥,现在想来是极美的画面。
那时后河的生态是极好的,河水清澈见底,小窜条不时跃出水面,翻晾着肚皮。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很多学生会下河摸鱼捉虾,我是从来不敢下去的,因为河里有我最怕的水蛭。但有的人似乎不怕,被水蛭叮了,一阵拍打就把它拍了出来。我刚来上学的时候,并未见过它,被叮了之后大呼小叫的狂奔一通,以为它和蛇一样有*,从此再也不敢下水了,尤其是舒缓温暖的地方。
板泉镇后河两岸居民家打的水井多是碱水,而后河两沿的泉水却是甜水,不能不说很奇特了。老板泉集就位于后河两岸河堤下面,板泉人形象的将逢集的地方称为河底。后河 的一处泉就位于老板泉集的饭市,集上熬牛肉汤的,卖白开水的都到这泉里汲水,就是在寒冷的冬天这处泉眼也不结冰,蒸腾的冒着热气。后来莒阿公路改道,将这处泉眼压在了桥下面,早已废弃。
随着城镇的开发,后河早已不再清澈宽阔,成了名符其实的臭水沟,随处可见生活垃圾圾和塑料袋。想想小时候后河河底还逢集,为什么没有这么多垃圾呢?我想与那时不使用塑料袋是分不开的,那时的人赶集都是自带提包、箢子盛装物品的。
二姨父不无神秘地说:“为什么板泉的影响大不如前了?就是因为那座桥盖住了泉眼,破了风水,泉眼泉眼,泉就是板泉的眼,没有了眼还能得好吗?”二姨父的话虽有迷信成份,但这样的流言能在百姓中流传,足见那处泉眼在老百姓的心中的地位。
没了老泉眼,板泉人又在后河上游发现一处新泉眼,近二十年来每日来此拉水喝的人络绎不绝。每逢过年,有老百姓会在泉眼的上方像压坟头那样用石头压上一方烧纸,以示祭奠。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在的板泉集又搬到了这处泉眼北面的树行子里,泉眼四周满是不堪入目的垃圾袋。家家户户现在也通上了自来水,想这泉眼也快完成她的使命了吧。
二、集市
提起板泉,当然最 的还是板泉集。板泉集自古以来就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集市,之所以如此闻名,我想与板泉便利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板泉地处岚济公路与莒阿公路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就是个通衢四方的要镇。板泉集逢五排十,年之前,买东西远不像现在这般便利,辖区内的采买活动几乎都要在这板泉集上完成,赶一次板泉集,比现在逛一次临沂都要难得。时过境迁,路越修越好,物流越来越发达。随着4G、5G网络的快速发展,随着智能机和各种APP的大范围普及,板泉也有了快递接收点、有了外卖。人们都懒得逛街了,习惯了坐在家里就把东西买了,板泉集早已不复昨日繁华。赶集也基本成了老年人的活动了。前段时间回板泉,赶板泉集的时候看见有几伙人奇装异服的在大集上搞直播,我不禁感叹:这个时代到底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真是稀里又糊涂。当哗众取宠成为一种时尚,是不是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
我记忆中的板泉集在前村东南角,足有百亩之大。因为赶集的人太多,后河的两沿是老集市仍然使用,赶集的小贩们远的有安东卫和赣榆来的。菜市、猪市、牛市、狗市、家具市、石槽市、条子市、饭市等五花八门一应俱全,五天一次的板泉集就是一场盛会,形形色色的故事不知在这里上演了多少。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吃食,粘牙的年糕、喷香的朝牌、焦*的牛蹄壳、酥脆的馓子、金*厚重的大锅饼、香到心脾的香果子、甜蜜的羊角蜜等一系列的美食,离开板泉你就吃不出那种味道。
最为热闹的时候是每年四月初五和十月初十的山会,那真是人山人海,用摩肩接踵来形容真是毫不为过。因为人太多,新集场、老集场的地方还不够用,营房靶场在这一天就成了家具市。光是耍把戏的就有好几帮,有杂技有动物表演。记得那时二姨父的侄子红旗三哥还很年轻,在耍把戏的门口卖票镇场子,他站在高处嘴里叼着烟卷,一只脚踩在收钱的小皮梢上好不威风。当然,受益的还是我们,可以免费看把戏。每年逢山会的时候,大人都会给我们几毛零花钱,买一枝冰棍,去看场把戏,就是童年 的娱乐。
板泉集的地位,也让很多板泉街上的青年好吃懒做,靠着在集市欺行霸市谋生。我就亲眼见过卖鱼的被一抢而空,卖羊的被柴头直接牵走,还有群殴打人的血腥场面。很多下边村里的人一提板泉街上的人,都大骂“马子”。而板泉街上的人都称呼这些人为“好佬”。
乡下的人想赶板泉集卖点大件的东西,若在板泉街上没个亲戚,那是万万不敢的,搞不好就被“好佬”抢去。而这些好佬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也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对外抱团,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些好佬们结队开着农用三轮贩大鹅去南京,一路上没有人敢拦截。对内呢,哪怕你再老实,他们绝不欺负板泉本街上的人。所以赶板泉集做生意,有个板泉街上的亲戚陪着,基本就平安无事了。也正因如此,要是在板泉街上能攀个亲戚,就成了乡里人的光荣。板泉街上的男人,不论好赖,找老婆都挑挑拣拣的,大都能找到个好老婆,乡下的女人嫁到了板泉街就意味着全家人不再受欺负。十里八乡,“板泉街”就是一张响亮名片,让人生恨又无人敢惹。
三、老屋
板泉的老屋都是集中建在后河两岸的,老屋的范围其实也就是老板泉的范围,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建筑向四周扩散,逐渐形成了前村、后东、后西、西庄四个村。在后河的南岸有一条贯穿板泉东西的大街,板泉街板泉街,我想大约就是由这条街而来,姑且就称她为板泉街吧。旧时富裕的人家大都沿街而居,各类商号、门市都在这条街上,我家的祖宅就位于这条街最核心的位置。
自90年代后期,国道和省道全面整修通车,商业重心也都随之转移到了这两条道路两边,老板泉街逐渐落寞下来。随着一些老人的故去,板泉街的老屋也大都空了出来,久而久之,破败颓废。即使如此,在还没有规划建设楼房之前,每次回板泉我都喜欢到这里转转。
老屋大多为夯土结构,连院墙也都是夯土的。只有前村姓诸葛的大地主家的房子是青砖青瓦的,古香古色,满满的都是年代的味道。二姨父家里的老祖在解放后就分得了一处地主家的青砖瓦房。我在那上学的时候,二姨家在村前盖了新房,老宅就成了菜园。小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就特别喜欢去老屋那边玩耍,老屋那时大都空了,土墙也不乏缺口,特别适合藏猫玩游戏。最窄的小巷也就1米宽左右,蒙上红领巾从土围墙上一跃而下,最能找到侠客的感觉。原生的、满树的家眉豆,捣点花生米一炒,就是一顿可口的美味。
在老屋的记忆里,画在老屋外墙的彩画给我的记忆最为深刻。二姨父说大地主诸葛家族有个孙子辈的人爱画画,这些画都是他在文革时期画的。要不是因为成分不好,上大学没份,当兵没份的,哪能打一辈子庄户,必定是了不起的人物。从小我就爱看这些画,以至到后来每次回板泉都要去那面墙前看看。小时爱看是因为仰慕,大了更多的是惺惺相惜。人的才华和金钱、地位大多是不成正比例的,真正能做到居陋巷不改其乐的又有几人?
老屋虽然破败,但各个院落中的树木却依然茂盛,一楼粗的树木比比皆是。有梧桐、有皂角、有洋槐……,到了盛夏那真是绿树成荫,满街飘香。女儿刚满月的时候,脖子下起满了湿疹,已有些流水糜烂,抹了很多药膏也不见效。二姨说去老宅子刮点雨水冲刷过的城墙土粉末撒上就好使。母亲很快找来了,妻子却怎么也不让用,说那土都冲刷几十上百年了,细菌该有多么大,直说我愚昧。我背着妻子,偷偷地给女儿用了几次,竟奇迹般的好了。
四、营房
板泉不同于一般的乡镇,在上世纪这里驻了一支部队。每日部队的起床号定时飘扬在小镇上空,当兵的人开始跑操了,小镇的人们也开始了这一天的忙碌。
部队营房就在板泉中心小学的北面不远的地方,所以学校里也有很多有*人的孩子。*人的孩子大都衣着新鲜、干净、整洁,他们的生活,我们这些土帽们是羡慕不已。学校的辅导员都由*人兼任,不忙的时候,辅导员常会来给我们上体育课,互动娱乐。当然最令我兴奋是能听到部队打靶和迫击炮训练时发出的声音。尤其是迫击炮训练时,感觉校舍都在震动,远远的似乎都能闻到让人血脉贲张的硝烟味道。童年的小伙伴小瑞,经常逃课,时常能从靶场捡些弹壳回来,把玩起来,真是爱不释手。
到了过六一的时候,学校经常会和部队在团部大礼堂联欢。联欢会后,部队会给全校师生放上一场电影,那热闹的场面时常会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氤氲。
“视人民为父母,把驻地当故乡”这宣传语当年就横贯在如今国道和府前街的路口的铁架上,部队于大多数的板泉人而言,都是抹不去的一缕芬芳回忆。
若是到了麦收等农忙时节,地里经常会看到当兵的帮老百姓干活,热闹的农忙场面就是对“*民团结一家亲”的 诠释。医院的医院,救死扶伤的标语清晰醒目,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的去那里看病,有就放,小来小去的没有就算了。现在想来,那时部队的存在也真是极大地便利了小镇的人们。当兵的会经常到街上购买日用品,他们并不讨价还价,做生意的见了小当兵的自是心花怒放。据说再早些年的时候,他们经常会主动到老百姓的家里干些掏粪之类的脏活,从不留姓名。
如今部队的团部已成为板泉镇*府的办公楼,当年的礼堂永远庄严肃穆,水塔的*姿依然挺拔。这里是我记忆里板泉变化最小的地方,每次我回板泉都爱去那里散散步,挽着妻子给她讲讲板泉的历史。
五、条编
条编是板泉人的传统手艺,由来已久,现在条编原材料多用柳条。柳条种植和柳编工艺是板泉的支柱产业,板泉也被冠以“柳编之乡”的美誉。鼎盛时期,各式各样的柳条筐远销日韩。但填满我的记忆的,却是看起来有些丑陋的腊条筐。
在还是比较落后的九十年代,人们对筐的工艺美并不感兴趣,主要是农用、家用,强调结实耐用,腊条筐才是 。
母亲的娘家刘岔河就是传统的条编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编。我的姥爷就是编腊条筐的高手,每一个板泉集,姥爷都会用独轮车推着他用腊条编的长筐、提篮来赶板泉集。只要姥爷来赶集,每次散了集,都会给我们这些孩子买点好吃的,来二姨家吃顿午饭。二姨勤劳节俭,很少给孩子买零食,靠了一集空的我和二姨家的三个表兄弟妹们,对姥爷的到来自是欢欣雀跃。
后来,苍山大蒜畅销,用腊条编的大蒜筐供不应求。姥爷所在的刘岔河村家家户户编大蒜筐,利润颇为可观。近水楼台,二姨哪肯错过这挣钱的机会。那年,二姨父出去打工,二姨就领着我和她家的表哥编大蒜筐。我和表哥打底锁沿,二姨编花。每打十个底,二姨就奖我和表哥一包三鲜伊面,为了三鲜伊面,我和表哥干的是热火朝天。由于大蒜筐需求量大,对质量卡的不严,腊条又比较贵,为了降低成本,很多人就往腊条里掺棉槐条。那年暑假,晚上夜深的时候,二姨没少领着我们到公路两边去偷割当时作为绿植的棉槐条。干这个活不用三鲜伊面,因为回来可以边干活边看《新白娘子传奇》。
腊条的味道沉浸在记忆里,就是零嘴的香甜,就是白娘子的法力无边。
六、伙计
板泉人称呼好朋友为伙计,伙计不在多,在于真诚,板泉的伙计就是如此。不管多长时间不联系,只要见了面,那必定是“挖心掏肺千杯少,促膝潮拉到天明”。我在板泉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却也有几个这样的伙计。
现在大家都已是不惑之年,有混的有钱的,也有在家种地务农的,但只要聚在了板泉老家的那张八仙桌前,没有贵贱,一年到头不见,喝酒吹牛就是有拉不完的呱。大家的笑点依旧如初,就像大家小时光着屁股在大井里洗澡时一样。
记得有一次和朋去县城玩,在一家小餐馆吃饭。两人点了几个小菜,一人要了一瓶啤酒,边喝边聊。天文、地理、历史、时*、足球,一顿潮拉,引得饭店老板也不禁侧耳倾听,结账时直问我俩是不是一中的老师。朋一本正经的说是,待两人走出饭馆,不禁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朋做了建材的生意,经常和工地的老板打交道,吹不改色的本事也让他发挥到了 。
瑞离我们最远,去了东北,命运也最为多舛。十几年前他的眼睛就盲了,头些年回来,伙计们坐在一起,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倒是瑞很乐观:“没啥,我很看得开,别看我看不见,我干按摩也不比你们少挣,现在我每天都出去跳舞,就是你们也做不到吧!”瑞淡然地说着,仍旧是以前那样笑容可掬。瑞是能人,混社会可比我们混得明白。虽然盲了,但性格还真是和以前没什么变化,仍旧是好玩好动。伙计们渐渐释然,酒、欢笑、泪水持续到了凌晨。
岁月不居,只要伙计们在一起就永远是少年……
七、姑娘
就是那嫣然一笑,似山中吐蕊的小花,含着些许幽幽的馨香,轻轻地,吐露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芬芳;
就是那嫣然一笑,好似春天里的煦风,蕴着泥土特有的气息,柔柔地,呵送吹面不寒扬柳风的舒爽;
就是那嫣然一笑,似极了西天的云彩,妆着几分淡淡的红晕,悄悄地,展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风韵;
就是那嫣然一笑,锁定记忆*思梦萦,带着青春年少的惘然,渐渐地,明白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前因;
就是那嫣然一笑,别离了你呀,小胖猪!今生今世,再教我到哪里去寻找!
年,我们全家从东北迁回了板泉。我在板泉经营了一家化妆品店。男孩子卖化妆品,并不多见,从事这个行业自然会接触很多姑娘,小胖猪就是我最为忠实的顾客。
小胖猪,身材微有些胖,眼睛大大的,睫毛长而翘,一笑起来,就像小猪一样,脸圆圆的肉嘟嘟的,嘴巴一笑就会飞扬。记得她 次来店里的时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她要了一瓶小护士的乳,我见她的手有些粗糙,就问她:“你在家编小筐吗?”她一脸娇羞,满面红晕的说:“恩,帮俺妈妈编。”我顺手拿起一瓶护手霜:“提货时送的赠品,送你一瓶抹抹手”。“真是谢谢呀”,说着她就去兜里掏钱,“真是不好意思啊,没带钱,我回家拿吧,俺家很近,就在营房住”。我就感觉这个小姑娘真是可爱,连忙说:“不用了,不用了,你先拿着用就是,有空给我送来就行”。从未谋面,也不知那天我为何就把货给她了。
第二天上午,阳光很好。我在店门口晒太阳,就见她身着白色的羽绒服,从东边走来。远远的,她也看见了我,只见她的脸立马灿烂起来,看着她的样子我竞有些痴了,只觉得她好美好美。
之后的日子,她几乎三两天就要光顾一下我的小店,最长的时候也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很多的时候她并不买东西,就是找我聊天,我也特别愿意和她聊天,聊得久了,知道她小我四岁,才18岁,中专毕业在家待业。开始的时候我把她当小姑娘,后来却发现自己慢慢地喜欢上了她,又觉得比她大4岁,年龄差距太大。几经踟蹰,半年左右的光景,她去了公路收费站上班,就只有在休班的时候来了,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转过年,舅舅给我在日照介绍了工作,腼腆的我直到化妆品店关门也没有问她的名字,要她的联系方式。
工作后,由于交通运输工作的特殊性,工资不高,一年到头总是在值班值班,也就很少回板泉了。年节偶尔回去也是匆匆而归,在小镇的人群里,我渴望能再见到小胖猪一眼,却从未如愿。有人说,求不得是一种美丽,我想可能最美莫过想念吧!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进程,板泉如今也有了房地产开发,低矮的古老的夯土房不见了,一幢幢电梯洋房拔地而起,已初具城市模样。已成臭水沟的后河得以疏浚,虽不是原来那般清澈,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倒也显得旖旎多姿,美是美了,遗憾的是没有半点记忆中的影子。老屋拆迁一空,老树再无半棵。只有因为是莒南 *支部所在地而保留的老庙还在向来者讲述过往的板泉。
二姨家屋后面不到米的地方就是工地,曾经是主要道路的当街早已杂草丛生,车辆无法通行。“也不说拆,也不说不拆,没拆的排房户户都通了水泥路,就咱这一片,也没大有人住了,就剩了俺这些老家伙了。”二姨夫喃喃地说着。
其实改革也好,发展也罢,千人一面一刀切,我觉得不是 的方式。美丽乡镇,不等于全面城市化,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发展的同时也需要传承。建了那么多的楼房,到底是不是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
游走在城市的边缘,我总感觉自己像一叶浮萍,过了快二十年的城市生活,越来越觉得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我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努力地寻找来时的路,却怎么也看不清了……